arcadia文学作品(帕慕克新作红发女人中文版出版)
【编者按】《红发女人》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·帕慕克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,中文版日前由世纪文景出版。这部十一万字的小说是帕慕克所有长篇小说中体量最小的一部,中文版是根据2016年出版的土耳其语原版译出。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。和上一部作品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一样,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,这一次,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挖井人。《红发女人》仍然使用了帕慕克一贯偏爱的悬疑元素,故事围绕着三十年前的一个谜团展开。

奥尔罕·帕慕克
A
三十几年前,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,我们在一座小城市演出。一晚,剧团和地方政治团体的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,长桌的另一端是个跟我一样红头发的女人。一时间,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起两个红发女人同坐一桌的巧合。他们问着诸如概率是几分之几,是否会带来好运,预示着什么的问题。
“我头发的颜色是天生的。”桌子那头的红发女人说,既像是抱歉,又带着得意,“你们看,就像天生红头发的人一样,我的脸上,胳膊上都有雀斑。我的肤色白,眼睛也是绿的。”
所有人转向我,看我如何作答。
“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,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。”我立刻回复道。
我并不总是这样对答如流,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:“对您来说这是天赐禀赋,是与生俱来的命运,对我而言则是自主意识的选择。”
我没有继续下去,以免在座各位认为我傲慢自大。因为,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嘲讽和愚蠢地发笑。倘若不回答,沉默就将意味着我甘拜下风:“是的,我的头发是染的。”那样他们既会误解我的性格,还会认为我是个胸无大志的模仿者。
对我们这种红头发的后来者来说,头发的颜色意味着被选择的个性。一次染成红色后,我终生都致力于此。
二十五岁上下,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,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,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。持续三年的地下恋情,最终以年长我十岁的情人的离弃而终结。他是个有妇之夫,一个英俊的革命分子。然而我们在一起激昂地读书时,多么浪漫,多么幸福!事实上,我既生他的气,也理解他。因为我们的地下恋情曝光,组织里认识我们的每个人都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。他们说这会引起妒忌,结果对大家都不好。与此同时,1980年发生了军事政变。一些人转入地下,一些坐船去了希腊,又从那里逃往德国成为政治流亡者,一些进了监狱遭受酷刑。大我十岁的情人阿肯也在这一年回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身边,回到他的药店。而我讨厌的图尔汗——因为他看上了我,还诋毁我爱的人——则了解我的痛苦,并且对我非常好。于是我们结婚了,认为这样对“革命者家园”来说也是好事。
不过跟另一个男人谈过恋爱这件事成为我丈夫的心结。他认为自己因此才会在年轻人中没有威信,但却无法指责我“轻浮”。他并非像我已婚的情人阿肯那样是个迅速坠入爱河又轻易忘却的人。因此,他开始难以装作若无其事。他想象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,对他奚落挖苦。不久之后,他指责“革命者家园”的同伴不作为,跑去马拉蒂亚组织武装斗争。我就不讲他在那里试图唤醒的同胞们是如何揭发这个闹事者,以及我丈夫是如何被宪兵堵在溪边挨打的。
短短时间内,生命中这第二次重大失去让我对政治更加冷淡。有时想着,不如回自己的家,回到退休的省长父亲和母亲身边,却下不了决心。回家,就不得不承认失败,也不得不远离戏剧。找个能让我加入的剧团已非易事。与普遍观点相反,我想演戏不是为了政治,而是为了戏剧。
我留了下来,于是,正如奥斯曼时期赴前线与伊朗作战有去无回的骑士们的妻子们,没过多久我嫁给了图尔汗的弟弟。事实上,与图尔加伊结婚,鼓动他成立流动民间剧团是我的主意。就这样,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出乎预料地幸福。继两个失去的男人之后,图尔加伊的年轻、孩子气、牢靠似乎成为一种保障。冬天,我们在伊斯坦布尔、安卡拉等大城市的左派协会的大厅,在无法称之为戏剧舞台的会议室里演出,夏天就去朋友邀请的镇子、度假城市、军队驻地和新建的车间及工厂周边支帐篷。在饭桌上同时出现我们两个红发女人,是这岁月的第三个年头。这之前的一年,我才把头发染成红色。
事实上,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出于我身材高挑的考虑。“我想给头发彻底换个颜色。”那天,我对巴克尔柯伊的中年社区理发师说,但脑子里连颜色也没想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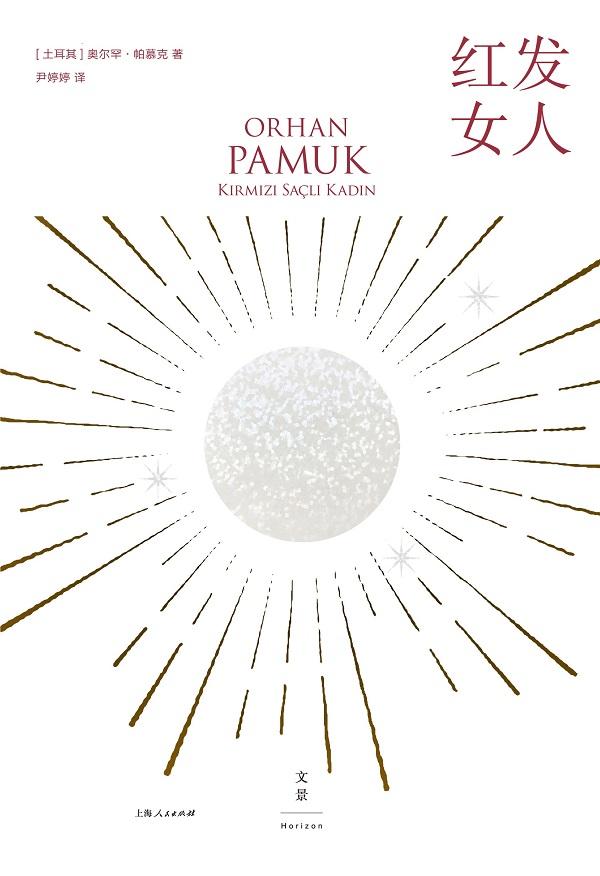
B
井底唯一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把带有贻贝、海螺、鱼齿的恶臭土壤装入桶中。也就是说,从干活的角度来说比上面轻松多了。然而困难不在于挖沙子、装桶和把桶送上地面,而是待在二十五米深的地下。
下潜时我便害怕了。一只脚踩在空桶里,两手紧紧抓住绳子,接近逐渐黑暗的井底时,我看见水泥墙的表面一闪而过的裂缝、蜘蛛网和奇怪的斑点,还看到一只惊慌失措的蜥蜴上下逃窜。地下世界仿佛在发出警告,因为我们把一个水泥管子插入了它的心脏。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地震,那样我就要长眠地下了。有时,我听到从地下传来嘶哑的奇怪声音。
“来了……!”马哈茂德师傅向我放桶时从上面喊道。
抬头向上看,井口显得那么遥小,我感到害怕,想立刻上去。马哈茂德师傅已经不耐烦了,我赶快一铲一铲用沙子填满桶,喊一声“拉!”。
马哈茂德师傅的力气远胜于我,他迅速地摇着辘轳把桶拉上去,小心翼翼地拽到一旁,卸在手推车上,然后立刻交还给我。
我纹丝不动,一直盯住上面观察这一切。如果能够看到马哈茂德师傅,我在下面就不孤单。马哈茂德师傅闪到一旁去倒土,井口立刻现出一块圆圆小小的天空。多么奇妙的蓝色!它是那么遥远而美丽,就像望远镜倒过来看到的世界。
直到马哈茂德师傅再次出现在井口向下放桶之前,我一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上面,欣赏望远镜另一端的天空。
过了很久,再次看到马哈茂德师傅像只蝼蚁般出现在上方,我才松了口气。不一会儿,桶落下来,我把它放到地上,冲上面喊:“好了!”
马哈茂德师傅去倒车里的沙土,他小小的身影一消失,恐惧立刻包围了我。万一他的脚被什么绊住,遭遇不测怎么办?万一他为了让我学规矩、长教训,一时半会儿都不出现怎么办?……如果马哈茂德师傅知道我和红发女人那晚的事,会想要惩罚我吗?
我挥了十来下铁锹把桶填满,紧张不安中,带着直奔地底的劲头又挖了一会。然而一时间,我的眼睛在黑暗和灰尘中什么也看不见。井底更加昏暗。白色的沙土异常松软。显而易见,这里不会出水。我们在这里白白担惊受怕,浪费时间。
出了井我就去恩格然找红发女人。图尔加伊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。她爱我。我要对图尔加伊和盘托出。也许他会揍我,甚至开枪。红发女人看到我大白天出现在她面前会怎样?
我靠着这点念想压制恐惧,把填满的桶向上运了三次后(我数了),又慌乱起来。马哈茂德师傅回到井边的速度更加缓慢,地下传来声响。
“师傅,师傅!”我冲上面喊。蓝色的天空跟钱币一样大小。马哈茂德师傅去哪儿了?我开始拼命叫喊。
终于,师傅出现在井边。
“师傅,拉我上去吧!”我喊道。
,免责声明: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,与本站无关。其原创性、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,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,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





